 2014-01-03
2014-01-03

陈克宇(艾群摄)
陈克宇:我是91届毕业生,1987年从湖南考进中国政法大学,是昌平校区的第一批学生。
我的高考成绩是我们县文科第一名,当时这个成绩能上北大,但为了稳妥报了中国政法大学。文革后政法大学第一年在湖南招生,而且在中国法律界有名气,法学家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会带来优势,所以就上了政法大学。
艾群:当初为什么选择学习法律?
陈克宇:当初选择学法律是比较明确的。我是农村的孩子,相比城市孩子来说多一些理想主义色彩,再加上湖南地域文化的特点就是理想主义色彩强烈。那时文革结束了,国家需要搞法治建设,我在上中学读了一些名人传记,发现很多大人物都是学法律的,这可能对我以后的发展影响很大,当时我还有一种从政的理想,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了我对法律专业的选择。
记得刚上学的时候,让我激动不已的就是看见学校拉出的条幅:“欢迎未来的法官、未来的政治家”。这真的是我当时选择政法大学的理想啊!因为80年代中期思想比较活跃,敢说这种话,现在估计不会再挂出这样的标语了。
艾群:学校每年都会挂出很感人的条幅。一般是“走进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享受最好的法学教育”
陈克宇:这反映了时代色彩,现在相对于从前而言,理想主义色彩要淡化很多,所以现在去政法大学的学生可能也不会像我们当年那样让自己和旁人激动。而且无论毛泽东时代如何,他把整个民族的理想主义追求推向国家的层面。可能当时人们的选择和思想没有那么多元,这是那个时代的局限,但那个革命时代的学生更多的带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
艾群:现在的学生比你们那时是少了一些责任感,更多的可能考虑的是四年之后的工作。
陈克宇:责任感肯定会差一些,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进步,但我只能说,那种时代的这种精神也是让人值得留恋的地方。
艾群:那当时来到昌平是什么感觉?
陈克宇:1987年9月份我来到昌平的时候是半夜,打着瞌睡去的,没什么感觉。第二天看到是一片工地,有点失落,因为工地毕竟是初创阶段。教学楼A、B才完工,C楼好像还没完工,宿舍楼只有三栋,很艰苦。宿舍楼当时都没取名字。
学校那种氛围给我一种处于高中延续阶段的感觉。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有得有失,法大87级这个群体比较有创意和冲劲儿!当时我们到昌平没有研究生,没有高年级,我们自己开创着整个校园文化,自己建立学生社团,形成我们自己的思想,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们87级的人在独立创新方面很突出,因为没有高年级学生对我们影响和引领,没有现成的社团,没有可以传承的同辈人的思想。一切靠我们自己。这情形也就给了我们一种机会,比如成立社团完全是自己设计。80年代中期的思想很活跃,各种政治、哲学流派、社会思潮处于探索阶段,还有那么大的政治波动,让人们从政治理想跌到现实中,那血淋淋的一幕,对我思想影响很大。
艾群:你们当时因为地域上的原因,是否缺乏与其他院校的交流?
陈克宇:我们与城里的院校的交流少了些,确实是遗憾,当时都觉得法大的法学还没成气候,学术氛围差了一些,所以学校有意识地请专家搞讲座,我们学生自己也会注意看一些报纸、杂志,大家都有意识地做一些弥补,培养自己独立的思维方式。
艾群:当时您四年是什么样的状态下度过的,我主要指的是自己的发展方向、定位、目标。现在的学生我了解一些,他们上大一的时候很迷茫;你们当时上大一的时候,是不是对自己有很明确的目标和要求,给自己制订了计划?
陈克宇:我算是给自己制定目标和计划的,因为当时我是带着从政的理想来政法的,不想死读书,所以第一学期时跟高中时候的学习方法比较接近,但第一学期结束后我做出了一定的调整,觉得不能这样读书。
艾群:高中的学习方法是什么?背书?
陈克宇:不是,就是以课程为统帅的学习,但是大学读完第一个学期后,我觉得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感兴趣的东西是在自由阅读和思考中的,所以对考试成绩就没什么追求了,从第二个学期后就不再把成绩看成一个很重要的追求。
艾群:那您是很有雄心、有理想和抱负的人吧?
陈克宇:可以这么说吧,比较有理想和追求。
艾群:那后来实现了吗?
陈克宇:没有,我分到了机关,放弃了。有些事情是需要时间的,机关的氛围很压抑、沉闷,我更多的是想追求思想上的自由,关注今后的发展,同时也关注社会的走向。后来到被分配到长沙大学教书,同时自学经济学。
艾群:那后来您怎么到这边来了呢?
陈克宇:在长沙大学,我还延续了在北京的习惯,就是关注国家的政策和走向,我总是第一时间看报刊,1991年底我读报时在只言片语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感觉出国家政策会有一定的变化。于是我决定辞去长沙大学的工作,给校长留了一封信,表示很抱歉。
辞职以后到海南工作了一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一家海南的房地产公司,当时海南的房地产很火爆,但是去了不久就搞宏观调控了,觉得房地产发展有限,所以1993年就去了北海,做律师,做了很多法律方面的工作,正好房地产泡沫后有几年的纠纷期。
艾群:那为什么到广州来了呢?
陈克宇:不是,当时想北海那边搞企业,认为做企业比较符合我的思想,因为觉得律师主要是个人性的服务,另外律师团队性差一些,我的长处是组织一个队伍,所以觉得做企业更适合。一方面是赶热潮,另一方面是觉得在后发地区才有白手起家的机会。所以到南方的第一站不是深圳是海南,海南房地产泡沫后又去了北海,因为不是想做律师,所以没有选择中心城市,而是后发地区。但在北海偶然的机会让我做了律师,后来发现这个职业适合我,我有这个特长而且也热爱这个职业,虽然当时经济效益不是特别好,不如做企业家,但作为一种职业选择来说经济待遇也算是不错了。
当时北海经济不景气,干了几年后,觉得可以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在法律服务方面要有所成长,达到一定高度需要到一个中心城市,后来我经过思考和对比选择了广州。
艾群:您觉得这些年来走的很顺利与法大有关系吗?比如在法大形成的思维方式、人生观啊,是不是您对生活很乐观,充满了信心?
陈克宇:是的,法大给了我很多精神财富,其实我出来白手起家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像我做出这么多选择,要经受很多煎熬,要有坚强的意志,要有积极的追求和精神上的支持。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我的精神支柱是——当时在法大上罗马法课的时候,江平教授给我们分析罗马法的精神,他说,“害之所归,利益随之。”在我困难时,我反过来思考这句话,作为自己精神的支撑。
艾群:和我们“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很相似,那您是否在频繁的奔波和艰难困苦中,对自己说,我是政法大学的学生,我这么优秀,我能渡过这一关。
陈克宇:绝对有。我的家乡在湖南长沙周边,那里产生了很多农民企业家,他们做的很出色,我觉得他们能吃的苦我都能吃,他们能做的我都能做,而且我有他们所没有的学识和眼界,他们是在生活所迫或者机遇所赐的情况下起家的,而我是经过认真的思考和抉择开始迈步的。当然也不免有一些年轻人的冲动,比如给长沙大学校长写辞职信时,就有一种冲动;当然也有一种对未来社会走向的判断,当时私下里跟朋友开玩笑说,我们这些未来的新型资产阶级怎么会在乎那些铁饭碗!当时觉得我们必须要在社会的未来走向中不被淘汰,走向前列,甚至引领这个潮流。
艾群:那您当时想成为政治家的理想相对于最后的选择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即使您法律服务做得很好,可能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您怎么看待当时大学时代的理想?
陈克宇:我觉得那时的理想还是很宝贵的一笔财富,我跟很多人说,理想和目标的价值不在于实现本身,而是给人一种驱动力。在小的时候必须有某种追求,从前的学习多是理论性和规律性的,而做律师可能是在我所拥有的条件下最接近我的最初理想,比如我给政府做过法律顾问服务,我在服务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对社会的政治理想,比如如何让政府依法行政,如何使管理人性化、更好的服务社会等,提出一些引导的建议。另外就是在行政管理方法方面,比如当时北海地产泡沫破裂后遗留了很多问题,政府想做一些土地盘整,但没有吸引力,领导就组织社会各界座谈,包括中介组织,当时我们得到邀请,我预感会有机会,当时本来要去武汉工作,我就推辞了那边的工作,留下来参加座谈,在座谈会上发表了我自己的看法,觉得意犹未尽,会后找主任接着阐述我的看法,于是主任要我写研究报告,根据这份研究报告政府将我作为土地盘整的法律顾问,当时我只是个26岁的小青年,能给政府提建议出主意,我还是很自豪的,能将自己的思想和想法付诸实践,这其实也是实现我的政治理想。其中我对政府的一个重要建议是,当时很多房地产交易按照法律是无效的,但是这样的话打乱了多年来形成的财产、交易关系,对社会造成重大的震荡。在这之前,北海有个很轰动的事件,是房地产纠纷,那个交易合同按法律规定无效,但法官判决有效,得到了企业界的一致好评,因为如果判决无效则整个北海经济都完了,且不利于政府的招商引资。我给政府的法律意见是:这些合同虽然无效,但因合同引起的法律关系应该给与确认,这对社会秩序起稳定的作用,对政府的信誉也有好处,况且还有前面的案例可以参照。所以这些无效合同在这个时候应该把它当作有效合同对待。这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转换为政策。这是很考验法律知识和法律智慧的,而政法大学给了我思想的积淀,当时学习西方法学理论,有些同学不感兴趣认为对以后搞实务没用,但我却很感兴趣,思考了很多,它给了我许多理念,比如对于什么是法,新兴主义法学派的观点:“法无非就是法官的观念”,法大能带给我们一些国外的理念,这对我的影响很深,是无形的。后来我从北海来到广州,有一次法大的刘全德教授来广州,我接待他,就和他讲起这个故事,他听了很高兴说:“你是个好学生,能把学到的东西用到实际当中,我的课没有白讲。”
在学校的时候我参加了很多社团,这些社团与我的政治理想有关。那时我就想,我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应该思考如何促进社会进步,社会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进步。但是在文革结束后没多久,改革开放刚开始,还把一些民营企业家和外商独资企业当成异类来防范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记得当时江平在讲罗马法的社会背景时候说,罗马法的形成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背景,恩格斯对罗马社会的论述是,一定的市民社会就决定了相应的政治国家。我是深受法律要和当时的市民社会相适应理论的影响。因为有这些思想和追求,在参与社会建设时,注意引导政府的工作如何更加合理化,更符合群众的需求。另一方面就是在为企业服务时,在劳资关系中,我们也会引导老板对民众不要过分压榨;也会做一些对企业家的思想进行提升的工作。为了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走向成熟,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保持社会和谐,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义务劳动和志愿活动,这些都是让我很自豪的。
艾群:我从您的言语中觉得,您以前的理想可能很模糊,后来将这种理想放在很现实的工作当中,一点点去实现,理想似乎更看得见摸得着了。
陈克宇:对,我当年的那种理想没有背离和放弃,我做事一直都很有激情,我现在是广东省工商联维权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在广东省的民营企业投诉中,为他们做了很多服务工作,我现在的社会政治活动和这类的社团有关,还有在民营企业投诉方面提供意见和帮助。
艾群:想问一下,在学校中除了江平教授给您影响很大外,还有哪些老师对你的影响很大?
陈克宇:如果是思想影响最大还是江平教授,他给我讲了一个学期的罗马法,那些东西让我至今这么清楚的记得,并且20年间对我的工作有很大帮助。
艾群:您对哪些课有兴趣?
陈克宇:我对思想史、政治学、法哲学理论比较感兴趣。当时有些老师,到现在我还印象很深,比如讲政治学的几个老师,白希、缪小飞、李小泉。还有法制史的郑勤老师、西方法理的刘全德老师。总觉得法大给了我很多宝贵的思想,还记得当初开国际关系史,法学学生感兴趣的很少,但是我选修了这门课程,当时是姓孙的女老师给我们上,她讲的内容让我对国际关系史了解很多,比如怎么样从这样的民族国家走向成熟,国际关系原则的确立等。我觉得一个企业、一个个体在社会上如何确立,很多东西跟那些课上讲的东西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艾群:那时候的校园正在建设当中,那样一种状况,对你们的学习生活有什么影响?
陈克宇:当然有影响,在“工地”上谈女朋友都没地方呆,呵呵,开玩笑。至少理想中的高校应该是充满诗情画意的,让你有灵感,还能轻松的在里面生活。而我们是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校园广播中播放“献给爱丽丝”都没有感觉有美感;待我感受到钢琴曲的美感已经在大三快读完的时候了,可能也是那段时间之前是学术理论的研究,比较煎熬,后来情绪相对平稳了之后,心里更加宁静平和了,觉得校园音乐美起来了。
艾群:现在明白了你们那届为什么捐献雕像“拓荒牛”,当时您回去了吗?
陈克宇:回去了。
艾群:学生们都喜欢拓荒牛。
陈克宇:都喜欢么?呵呵。
艾群:都喜欢,拓荒牛已经成为学校最好的标志了。
陈克宇:我想通过这个访谈说说我们同学之间关于拓荒牛的小故事,可能有点跑题。当时张波作为组织者负责这事,包括创意、雕塑。样子出来了,我们从各个角度观察都看不出这头牛的性别,我们问张波,他乐了说:“肯定是母牛啊!因为我们的牛有两个寓意,一个是拓荒,因为我们87级是昌平的第一届,第二个要反映我们87级最“牛X”,所以只有母牛才能兼具二者!”大家都乐了。我们87级是有思想有创意的一群人。
艾群:当时捐了多少钱啊?
陈克宇:至少有十几万吧,当时我们每个人可能出了200多块,我们那届有800多人,请了一位美院的教授设计的。我觉得这个拓荒的定位很好,演绎我们要做中国法治建设的拓荒牛。
艾群:做律师要有激情么?
陈克宇:要有的,要有激情要有感染力,还要有坚定的信念。如果没有激情,律师职业是很无聊的,支持不下去。律师的压力出奇的大。我当时做律师的时候政治环境不太好,我们都像个心理医生,连自己的心理都调试不了的话更没办法调试客户的心理。
艾群:那您后来在法大上完本科后,有没有再进修些什么?
陈克宇:没有,但是我做了一些自学,自学了经济学,当时想考北大的国民经济管理的研究生,但是后来准备不够,下海了。但是经济学中的很多东西对我有很大的益处,自学对我后面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崔诗婉整理艾群编辑)
陈克宇,1991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曾先后在长沙大学、新华社海南分社、海南乐普生置业有限公司、远东律师事务所(司法部部级文明所)及其北海分所从事高校法学教育、新闻、企业法律服务和律师工作。1998年转入广州执业,为广东国声律师事务所(原名“广东证券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任该所合伙人会议主席。2001年6月,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自1994年至今,兼任“北京思源破产与兼并咨询事务所”客座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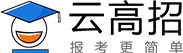
 收藏
收藏
 分享
分享
 生成海报
生成海报
 点赞
点赞
 446
446

